《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以下簡稱“《新加坡調解公約》”或“公約”),是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歷時四年研究擬訂、并經聯合國大會會議于2018年12月審議通過的國際公約。2019年8月7日,公約在新加坡開放簽署,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46個國家和地區作為首批簽約方簽署了這一公約。
繼新加坡與斐濟批準《新加坡調解公約》后,卡塔爾已于2020年3月12日完成了公約的批準加入程序。鑒此,該公約將于2020年9月12日起生效。
《新加坡調解公約》有其相應的適用范圍。哪些協議屬于公約下的和解協議,哪些則不屬于公約的適用范圍,筆者在此作一些討論介紹,以期增進大家對公約適用范圍的進一步了解。
一、公約適用于因調解產生的“SETTLEMENT AGREEMENTS”
通過公約的英文名稱,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調解公約》是一個適用于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的國際公約。換言之,《新加坡調解公約》適用于調解所產生的、當事人為解決商事爭議而以書面形式訂立的協議,即Settlement Agreements。公約以括弧所明確的“Settlement Agreements”,表明這樣的協議不是其他的調解協議,它是也僅僅是一種和解協議,英文用語為“Settlement Agreements”。公約這樣的用語,旨在區別于其他的“調解協議”。一般而言,調解協議通常指的是當事人同意將其爭議交由第三方調解的協議,譬如新加坡調解法下的Mediation Agreement, 或者香港調解條例下的Agreement to Mediate。
這里“From”的“Mediation”,按照公約的要求,是指“不論使用何種稱謂或者進行過程以何為依據,指由一名或者幾名第三人(調解員)協助,在其無權對爭議當事人強加解決辦法的情況下,當事人設法友好解決爭議的過程”之調解。
公約下的調解是第三人(調解員)協助性質的調解,不同于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體制。應當說,我國《人民調解法》下的人民調解法律制度“行政色彩濃郁”,側重于國內爭議特別是民事爭議的化解。同時,公約下的調解,與我國《民事訴訟法》下的法院法官主持下的調解或者《仲裁法》下的仲裁庭的調解亦有不同。這種不同,究其實,就在于進行調解的人員是否“無權對爭議當事人強加解決辦法”。
二、公約適用的和解協議是INTERNATIONAL的
根據《新加坡調解公約》第1條的規定,通過調解而達成的和解協議,必須是國際性的,即International Settltement Agreements,它要求這樣的和解協議在訂立時具有國際性,因而排除通過調解達成的國內爭議的和解協議。
確定一份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是否具有國際性,公約規定了營業地、實質性義務履行地和最密切聯系這三項考量指標。如在和解協議訂立之時,至少有兩方當事人的營業地位于不同國家,或者協議各方當事人設有營業地的國家與和解協議所約定的實質性義務履行地所在國不一致,或者協議各方當事人設有營業地的國家并非與和解協議主體事項關系最密切的國家,則該和解協議具有國際性。
為進一步明確相關營業地的涵義,公約第2條第1款進一步規定:
(a) 一方當事人有不止一個營業地的,相關營業地是與和解協議所解決的爭議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同時考慮到訂立和解協議時已為各方當事人知道或者預期的情形;
(b) 一方當事人無營業地的,以其慣常居住地為準。
由此可見,國內的和解協議不在公約適用的范圍以內。同時,與《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下仲裁裁決作出地對該公約適用有重大意義不同之處,在于和解協議作出地不是《新加坡調解公約》適用的要求。也許是基于這種考慮,《新加坡調解公約》沒有規定是否允許互惠保留。
三、公約適用和解協議下的爭議是商事性的
《新加坡調解公約》適用于和解協議下的爭議是商事性的,其序言“認識到爭議當事人請第三人協助其設法解決爭議的商事爭議解決辦法對國際貿易的價值”段中業已作了明確表述。
按照《新加坡調解公約》第1條第1款的規定,經過調解產生的和解協議是當事各方為解決商事爭議而訂立的,因此,公約適用于跨境商事爭議下的和解協議。
盡管公約并未對“商事爭議”作出釋義,但是,在其第1條第2款中用窮盡式的除外方法,規定了排除適用的兩方面事由:一是為解決其中一方當事人(消費者)為個人、家庭或者家具目的進行交易所產生的爭議而訂立的協議,不適用公約;二是與家庭法、繼承法或者就業法有關的協議,不適用公約。
也就是說,對于個人、家庭等私人目的的交易所產生的糾紛、消費者糾紛和婚姻家庭、繼承法或者勞動法有關糾紛的和解協議,公約明確予以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
四、公約適用的和解協議應當采取書面形式
《新加坡調解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本公約適用于調解所產生的、當事人為解決商事爭議而以書面形式訂立的協議(“和解協議”)” 。在這里可以看到,書面形式是公約對為解決商事爭議達成的和解協議的形式上的要求。口頭協議不具備可以為公約所適用的協議形式。
對于何種形式為符合要求的書面形式,公約采取的則是較為寬泛的做法:和解協議的內容以任何形式記錄下來即為“書面形式”。電子通信所含信息可調取以備日后查用的,該電子通信即滿足了和解協議的書面形式的要求。
另外,公約要求的書面形式應當是可以證明的。顯示和解協議產生于調解的證據,既有調解員在和解協議上簽名,也有調解員簽署的表明進行了調解的文件以及其他可以證明書面形式存在的文件。如果和解協議是用電子或者其他任何可被固定記錄下來的方式的,公約參考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法規所體現的功能同等原則,具體體現在公約第4條第2款。
應當看到,公約旨在解決國際商事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的跨境執行問題,而要解決跨境執行,首先需要有執行的依據。這一執行依據,至少必須是清晰明了、符合公約規定的書面形式的和解協議。
五、與訴訟、仲裁關聯的協議,排除在公約適用之外
《新加坡調解公約》適用于因調解而產生的、解決商事爭議的和解協議,但同時也明確公約不適用于以下和解協議:
(一) 經由法院批準或者系在法院相關程序過程中訂立的協議;和
(二) 可在該法院所在國作為判決執行的協議。
另外,公約還明確,對于那些已記錄在案并可作為仲裁裁決執行的協議,也不適用。
這一點,對于我國需要引以特別注意。因為,在我國《民事訴訟法》體制下,法官主持下調解達成的協議,或者訴調對接中心主持下調解達成的協議,與公約適用下的和解協議是不同的。這里的關鍵在于,對于通過調解當事人達成的協議,調解員是否加入了調解員在主觀上要求的解決辦法。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下,這種“強加的解決辦法”似乎在所難免,有亦自然。但是,按照公約的要求,調解員無權強加爭議的解決辦法。我國《仲裁法》下的仲裁庭調解,亦或多或少地存在類似的問題。而這,恰恰就是公約排除在訴訟中經調解達成協議后做出的包含和解內容的可執行的法院判決和在仲裁中經調解達成協議后做出的包含和解內容的可執行的仲裁裁決(即Consent Award)適用的道理所在。公約的這一做法,是旨在避免公約與《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和《紐約公約》等公約發生沖突適用之情形。應該指出的是,公約不能僅因為法官或者仲裁員參與調解過程就將和解協議排除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外,否則既可能會出現一方面根據國內法無法執行,另一方面又無法通過公約獲得執行救濟的情形。
六、 公約允許締約國對和解協議適用上所作的保留
在國際條約的締結和參加過程中,國際條約通常有一個關于條約適用的聲明保留的規定。《新加坡調解公約》也不例外。
公約允許締約國對以下兩種情形予以保留:
(a) 對于其為一方當事人的和解協議,或者對于任何政府機構或者代表政府機構行事的任何人為一方當事人的和解協議,在聲明規定的限度內,本公約不適用;
(b) 本公約適用,唯需和解協議當事人已同意適用本公約。
換言之,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簽署了《新加坡調解公約》,但在批準加入的時候,我國政府可以就政府機構或代表政府機構行事的行政當事方參與的和解協議作出相應的聲明保留,也可以就和解當事人是否需要在和解協議上或者其后達成的某種協議上作出同意公約適用的書面意思表示的問題作出某種聲明保留。當然,必須注意的是,除了以上明確授權的保留外,公約不允許作出其他任何保留。
公約以及任何保留或者保留的撤回僅適用于在本公約、保留或者保留的撤回對公約有關當事方生效之日后訂立的和解協議。也就是說,公約對于締約國在其批準加入且公約生效后訂立的和解協議可以適用,對于締約國所作的任何保留或者保留的撤回生效之后訂立的和解協議,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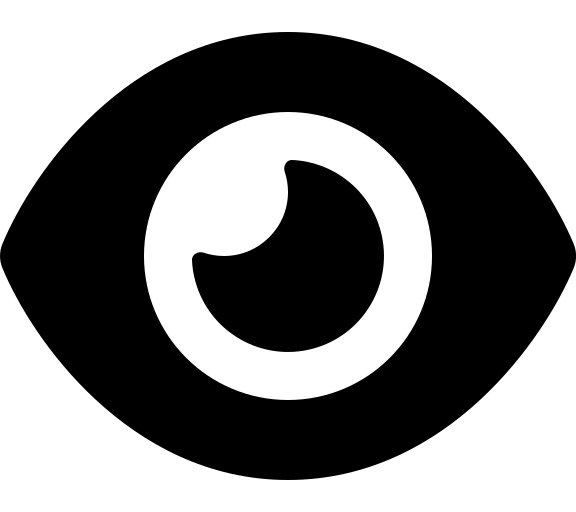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